
+
-
成熟大叔
温柔淑女
甜美少女
清亮青叔
呆萌萝莉
靓丽御姐
“这样啊。我看你希腊语说的挺流利的,原来是老熟人。”太后点点头。
“我的启蒙老师曾经是塞维利亚的居民,同样是逃难到突尼斯的。”穆罕默德说起了自己的师承:“我们这群人,学习伊本·路西德的学说,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,所以对希腊语也算熟悉了。”
“另外我也懂一些拉丁语,因为我们经常和罗马、帕多瓦等地的大学交流。他们一直很喜欢我们这一派的观点,所以两边的交流挺多的。哦,按照拉丁名字,我们应该叫阿威罗伊学派。”他介绍道。
“不过说是启蒙,其实我那会儿年纪也不小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苦笑道:“哎,年少时无知,浪费了太多时间了。”
“那你是怎么到叙利亚去的啊?”太后颇有兴趣地问。
“整个北非,相互来往都很紧密的。那里没有太强大的统一王朝,倒是有很多零散的部落和诸侯。学者们经常在各个埃米尔们的宫廷间往来,充当客卿。”穆罕默德说。
“我本来在摩洛哥暂住,等学习有了些起色后,承蒙老师看重,就推荐我去突尼斯,师从博学的伊本·赫勒敦阁下。不过,可能是从政道路上经常遭遇挫折,所以赫勒敦老师的思想比较激进,在当地敌人也多。所以,他就应邀去了思想更开放的埃及,最后还到了叙利亚讲学。”
“帖木儿劫掠叙利亚的时候,一批学者出面请求他收敛一些,赫勒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。帖木儿和他交谈之后,很敬重他,于是只收了钱就走了,没有屠杀城镇。这让他在当地出了名,于是更多人开始邀请他四处讲学。贵国接收叙利亚几处领地的时候,我们也受邀去过,就是在那边结识各位的。”
“他提出了什么学说啊?”太后好奇地问。
“他的学说应该源于穆尔太齐赖派,这一派的核心思想是早期的‘意志自由论’和来自希腊的唯理主义。”穆罕默德说。
“穆尔太齐赖派认为,胡大是唯一的主宰,通过理性创造了这个世界。由于神具有‘统一性’,所以祂是全知全能的,也因此不存在本体之外的各种德行,也就是说,是不能人格化的,也不可能在天国中被信徒们看到。”
“同时,因为神是独一的,所以经书是神创造的,而不可能等同于神,也就因此不具有神才独有的无始、永恒、不缪的特征。说的通俗点,就是经书不是神,所以可能存在错误,也可以进行纠正。”
“另一方面,他们坚持认为,胡大是最公正的,所以并不会预定人类的行为。人拥有无限自由的意志,人的行为也完全凭借自己来进行,神则对人类行为的善恶进行裁决,而决定赏罚。因为这个观点,他们也被称为‘公正派’。”
“他们也推崇理性,反对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,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原则,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前提。如果丧失了理性,就会屈从于邪恶,而丧失自由。所以应该重视理性哲学的修行,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以知识和理性,达到‘正信’的境界。”
“这个学说受到了哈里发马蒙——也就是‘智慧宫’创立者的支持,一度成为显学,开始主动对经书进行注解。但后来因为政治斗争失败,遭到了打击和驱逐。不过很多人来到了相对边缘的地区,比如安达卢西亚,继续进行研究和教学。”
“我的天父啊,我确定这是位哲学家了。”太后看了看王大喇嘛,又放弃似地摇摇头,看向郭康:“你应该能听懂吧?我已经晕了。”
“这和我们这里,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说,是有很大共同之处的。”郭康回答:“还好,能听得懂。”
“其实还是有不少区别的,只能说这个学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,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,还是有冲突的地方。”“老海胆”说。
“亚里士多德认为,神是不变的‘第一推动者’。但公正派很重视对于有限与无限、永恒与静止等概念的研究和辨析。他们分析之后认为,世界不可能是永恒的,也不可能一成不变。这一点,也是个老争论话题了。”
“那伱的老师怎么看?”郭康问。
“我的老师倾向于研究历史。”穆罕默德见他听得懂,也来了劲:“他早年也试图从政过,还很精明能干。但因为各种原因,每次到关键时刻,都会遭遇失败,只能在各个埃米尔国之间来回跑。”
“后来他灰心丧气,决定专心研究学术,又遇到了亲人因海难丧生的打击。可能是遭遇的苦难太多,他痛定思痛,开始努力收集资料,编纂史书,试图研究出历史里的规律,找出国家衰落、文明遭受打击背后的逻辑。”
“他把这些研究成果,写成了《历史绪论》一书,教授给后学,号召大家通过可证实的史料,来分析研究现世中的逻辑,以人类本身为研究中心。至于宗教,则认为是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,应该交给胡大。人类自己,把大地上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——这个观点在当地,还是挺激进的。”
“那他研究出什么成果了么?”郭康问。
“他认为,历史本身是连续的、有前因后果的。把历史事件放在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,分析成因和现象之间的规律,再把这些逻辑关系联系起来,就有助于总结出治乱兴衰的规律。”穆罕默德说。
“他通过史料,努力找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律。比如王朝的兴衰,是有明显的周期的。在北非柏柏尔人的政权里,四代人就是一个明显的周期。可惜这个周期的适用范围不广,在更发达的埃及和安达卢西亚,就不是这样了。”
“为了解释这个问题,我们觉得,应该是因为不同地区,物质资源、气候环境等皆不相同的原因。这些地理环境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形式,社会形式又影响了国家的命运。我们可能需要更细致的研究,才能像医生看病一样,针对具体问题,给出解决病症的特定药方。”
“当然,就整体而言,他倒是确定地认为,天方教诸王朝的历史中,存在着重复出现的、周期性循环的现象。而且,这种兴衰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,并不受王公们主观意志的左右。”
“他因此认定,哈里发和苏丹们声称自己是胡大在世上的投影,实际上只是一种吹嘘。神的真正投影,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。而这些统治者,只是社会中的蛀虫,基本上都是在搞破坏。普通人的劳作和活动,才是推动历史演进和周期更替的动力。”
“当然,你也知道,这个结论肯定不太让埃米尔们高兴。”他摊摊手:“这些阿非利加的埃米尔们太保守了。我觉得他搬家到埃及,虽然说是为了亚历山大的图书,借此研究经济和社会的规律,但肯定也少不了这个因素。”
“也不错了。”王大喇嘛安慰道:“居然没抓他,只是施压,这已经比大部分拜上帝教国家好太多了……”
(本章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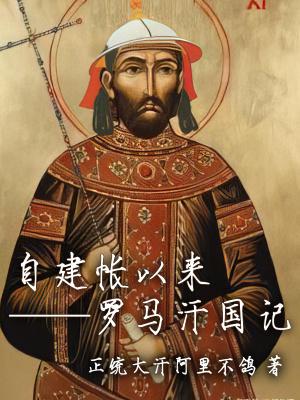
 登录信息加载中...
登录信息加载中...